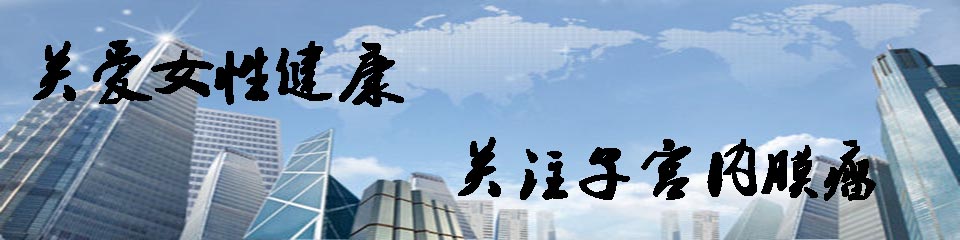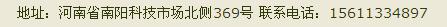子宫内膜癌早期诊断专题讨论-2
文章编号:1003-6946(2015)07-485-04
子宫内膜癌的流行病学及高危因素
杨 曦,马 珂,吴 成
(医院,北京102218)
中图分类号:R737.33文献标志码:B
子宫内膜癌在美国、欧洲等发达地区,目前已接近新发妇科恶性肿瘤的50%,2015年美国子宫内膜癌的新发病例54870例,死亡病例10170例[1]。近二十年,英国的子宫内膜癌发病率上升1.5倍,美国同期子宫内膜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升高1.1%和0.3%。在日本,近二十年来子宫内膜癌与宫颈癌的比例由1∶9现已接近1∶1,且有向年轻化发展的趋势。近年来,我国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习惯及饮食结构发生了很大改变,随着代谢性疾病的增加,子宫内膜癌也出现了发病率升高和发病年轻化的趋势。我国2004~2008年中国肿瘤登记的数据表明,子宫肿瘤发病率上升为1.5倍。北京市肿瘤登记办公室数据显示,2001年以来子宫内膜癌发病率明显高于宫颈癌,2008年后已成为发病率最高的女性生殖道恶性肿瘤[2]。根据子宫内膜癌的病因学和流行病学资料[3],本专题将子宫内膜癌的高危因素大致分为四类进行探讨:一是与遗传物质相关;二是解剖和生理处于基本正常的情况;三是明显的疾病状态,即内源性雌激素影响;四是外部的因素。
1 遗传物质相关高危因素
子宫内膜癌在白种人中发病相对风险度为2,在北美及北欧相对风险度为3~18[4]。子宫内膜癌的发病率有明显的种族差异和家族遗传倾向,而现在的分
子生物学研究表明,遗传因素在子宫内膜癌发生中有很大作用。研究表明,与无恶性肿瘤家族史女性相比,恶性肿瘤家族史患者患子宫内膜癌风险为2.1,这
表明一级亲属恶性肿瘤家族史与子宫内膜癌发病风险增加有关。
1.1 遗传性非息肉性结肠直肠癌(HNPCC)
遗传性子宫内膜癌占子宫内膜癌的2%~5%。HNPCC也被称为Lynch综合征或癌症家庭综合征,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有30%~60%的人类的DNA碱基错配修复(MMR)基因突变,倾向于并发多种恶性肿瘤,特别是结直肠癌与子宫内膜癌。女性患者中,子宫内膜癌发生率大于或等于结直肠癌,超过50%的HNPCC病例中,患者以恶性妇科肿瘤作为首发肿瘤。HNPCC患者发生子宫内膜癌的终身风险比其他患者高50倍。单基因突变的患者发生子宫内膜癌的终身风险波动在40%~60%。散发性子宫内膜癌患者中发现MMR基因突变频率为1.8%~2.1%,主要是MLH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造成了MMR的缺乏。HNPCC患者已经具有先天性的MLH1、MSH2、MSH6或PMS2的基因突变,如果患者子宫内膜细胞中再次发生基因的另一个等位基因缺失或突变(MLH1、MSH2、MSH6或PMS2),即会发生肿瘤形成。HNPCC患者子宫内膜癌发生较一般人群早发生10年。有18%~23%的HNPCC患者中发生子宫内膜癌小于50岁,在50岁以下的子宫内膜癌患者中,有9%的患者发生HNPCC相关基因的突变。美国癌症协会建议[5],HNPCC相关遗传突变已知和可疑携带者,从35岁开始,每年进行1次子宫内膜癌活检,建议可疑者进行遗传咨询以及基因检测,在完成生育后可以行全子宫及双侧附件的切除预防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已被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以及其他专家小组支持[5,6]。
1.2 PTEN错构瘤肿瘤综合征
PTEN错构瘤肿瘤综合征其中最常见的类型为考登综合征(cowden syndrome)也称为多错构瘤综合征,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病,具有乳腺癌、甲状腺以及子宫内膜癌的高危倾向[7],大约80%的考登综合征患者中检测到PTEN的突变,患者患子宫内膜癌的比率约5%~10%,而在一般人群中的风险为2.5%。
2 一般因素
2.1 年龄因素
子宫内膜癌的发病高峰年龄为50~59岁,中国女性发病平均年龄为55岁。有研究显示,大部分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发展为子宫内膜癌的时间在15年以内。日本将子宫内膜细胞学检查(endometrial
cytology test,ECT)应用于绝经后人群的子宫内膜癌筛查,并纳入老年人保健法。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对中国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地在内的研究数据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子宫内膜癌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相对风险为2~3[4]。
2.2 绝经及初潮因素
女性≥52岁未绝经者称为延迟绝经,延迟绝经者患子宫内膜癌的危险比49岁之前绝经者增加2.4倍,为45岁以前绝经者1.5~2.5倍。延迟绝经患者无排卵性月经周期缺少孕激素的作用,延长了雌激素对于子宫内膜的作用时间导致子宫内膜增生的发生。12岁或12岁以后初潮者患癌机会少于更年轻者,相对风险度为1.5~2[4],但不意味着越推迟就越降低危险。初潮早与绝经晚均接受雌激素刺激的机会增多,且均与排卵异常有关。
2.3 孕育因素
有研究显示,未孕者至少比生过一个孩子的人群增加2~3倍的危性[4]。在子宫内膜癌患者中,约15%~20%的患者有不育史。孕育问题伴随的子宫内膜癌发病风险增加仅仅局限于那些患有不孕的妇女,与没有生育问题的妇女相比,诊断过不孕症的患者发生子宫内膜癌的风险为1.7;而由于卵巢问题导致的不孕症患者,其发生子宫内膜癌的风险为4.1,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孕症患者尤其是无排卵导致的不孕症患者子宫内膜癌的发病危险会增加的原因,显然因持续雌激素作用,缺乏孕激素的对抗与调节,引起子宫内膜增生和癌变。
3 内源性雌激素增高的因素
3.1 肥胖、糖尿病及高血压 肥胖、糖尿病、高血压并称为子宫内膜癌三联征。
3.1.1 肥胖
26%~47%的子宫内膜癌可能与肥胖有关,肥胖患者发生子宫内膜癌的相对危险度是2~10,约有80%子宫内膜癌患者体重超过正常平均体重的10%。肥胖者发生子宫内膜癌机制推断为:①代谢因素:体内脂肪增加雌激素存储,缓慢释放入血同时缺少孕激素抵抗,而脂肪细胞可产生芳香化酶,使肾上腺分泌的雄烯二酮转化为雌酮,血中雌激素含量增加;②内分泌因素:肥胖患者具有内源性胰岛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IR),胰岛素代偿性增加致高胰岛素血症,从而雄激素水平升高,脂肪又加速雄激素向雌激素转化,结果导致雌激素增加;③饮食习惯:高热量饮食的摄入,素食者相比非素食者,性激素结合球蛋白(sex hormone-binding globulin,SHBG)水平升高,雌激素水平下降15%~20%,推断饮食影响机体雌激素代谢;④瘦素影响:瘦素是调节能量平衡、控制体重的关键因子,瘦素还作为有丝分裂原参与肿瘤的发生。可以影响PI3K/AKT通路参与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发展。
3.1.2 糖尿病
子宫内膜癌常伴发2型糖尿病,糖尿病患者患子宫内膜癌的危险比正常人增加1.2~5.6倍。高血糖使胰岛素代偿性增加致使发生高胰岛素血症。高胰岛素使雄激素增高的机制为:①胰岛素与位于卵巢的胰岛素受体结合,促进卵巢雄激素合成酶P450c17α活性增加雄激素合成;②胰岛素促使垂体黄体生成激素(LH)释放,致使雄激素水平升高;③胰岛素抑制SHBG的生成,使游离激素水平增高。高雄激素通过芳香化酶转化生成雌激素,促进子宫内膜病变的发生与发展。
3.1.3 高血压
高血压患者发生子宫内膜癌的相对危险度1.2~2.1。有研究指出,单纯高血压不增加子宫内膜癌的发生,但高血压患者常并发肥胖及糖尿病。肥胖并发的胰岛素抵抗不仅增加糖尿病危险因素,而且可致交感神经兴奋及电解质紊乱导致高血压的发生。糖尿病因胰岛素抵抗及高胰岛素血症导致脂质代谢紊乱加重,动脉粥样硬化形成,与肥胖、高血压形成恶性循环。而且胰岛素抵抗及高胰岛素血症可使血中雄激素水平升高,间接引起雌激素水平增加,致使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及发展。
3.2 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
PCOS的患者卵巢滤泡持续时间长,但不能成熟达到排卵,使子宫内膜处于持续的雌激素的刺激下,缺乏孕酮的调节和周期性内膜脱落,导致内膜发生增生改变。PCOS患者体内雄激素水平比正常妇女要高,雄激素可转化为雌激素导致内膜增生和增殖,进而发生不典型增生甚至子宫内膜癌。胰岛素抵抗和高胰岛素血症在PCOS的发病机制中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
①促进子宫内膜芳香化酶的活性与表达,促使雄激素转化为雌激素,促进子宫内膜增生的发生与发展;
②与内膜中胰岛素受体结合,促进子宫内膜增生;
③调节子宫内膜中雌激素受体(ER)的表达,使雌激素刺激作用增加。PCOS患者体内高LH、胰岛素和雄激素水平可以共同影响卵泡发育,长期无排卵可引起黄体功能缺陷,子宫内膜不发生周期性的增长脱落,雌激素持续刺激,可发展为子宫内膜癌。
3.3 功能性卵巢肿瘤
卵巢性索间质肿瘤包括颗粒细胞瘤和卵泡膜细胞瘤,部分浆液性卵巢肿瘤具有分泌雌激素的功能,能引起月经不调、绝经后出血及子宫的内膜增生和子宫内膜癌,相对危险度为>5[4]。卵巢肿瘤合并子宫内膜癌的机会为2.5%~27%,卵泡膜细胞瘤较颗粒细胞瘤具有更强的雌激素分泌功能,所以前者合并子宫内膜癌为后者的4倍,约25%的卵泡膜细胞瘤并发子宫内膜癌。
4 外源性雌激素因素
4.1 绝经激素治疗(MHT)
单独使用雌激素替代治疗可增加子宫内膜癌的危险性10~20倍[4],但若
联合孕激素不增加子宫内膜癌的风险[5]。但也有研究表明,如果曾用过雌激素治疗的女性,即使之后改用孕激素联合治疗仍存在高风险。
4.2 三苯氧胺
三苯氧胺(Tamoxifen,TAM)又名他莫昔芬,为非甾体类抗雌激素药物,广泛应用于ER阳性乳腺癌患者的内分泌治疗。TAM作为一种选择性受体调节剂,在不同靶器官其作用不同,在乳腺中具有抗雌激素作用,但在子宫内膜中具有弱雌激素作用。应用TAM者与未应用者相比,发生子宫内膜癌相对危险度为1.7~3.6[4],故建议常规进行筛查。
5 其他因素
有过盆腔放射治疗的其他恶性肿瘤的患者发生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增加,可能会影响DNA造成Ⅱ型子宫内膜癌的发生[5]。有研究显示,宫内节育器的使用(含有或不含有激素)、哺乳、吸烟、茶和咖啡的摄入
6 结 语
研究子宫内膜癌高危人群的意义在于浓缩子宫内膜癌的筛查人群,使得筛查出阳性结果的比例增高,降低社会卫生经济学成本,在2015年的美国癌症协会指南中推荐[5],平均风险或者高风险的女性(包括高龄、无抵抗雌激素治疗、他莫昔芬治疗、绝经晚、不孕不育、无排卵、肥胖、糖尿病、高血压),建议患者在围绝经期出现出血症状需要就诊。35岁以上具有以下高危因素的患者,包括①HNPCC突变;②明确突变携带者;③缺乏基因检测结果,有可疑常染色体遗传病(肠癌)需要每年进行筛查,可以考虑用子宫内膜活检的方式进行筛查。但在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中无子宫内膜癌的筛查建议[9]。日本妇科肿瘤协会发布的指南[10]针对年龄50岁以上或绝经后,最近6个月内有异常出血症状的女性进行子宫内膜癌的筛查。关于筛查的间隔无明确标准。子宫内膜癌风险(未婚、未孕、绝经晚、初婚或孕年龄较高、孕育次数少、30岁以后月经不规律、使用过雌性激素、糖尿病史、高血压史、肥胖等)的人群,在医生的判断之下进行筛查。推荐筛查的方法为子宫内膜细胞学法。除了进行积极筛查之外,对于可控的高危因素,如糖尿病、肥胖等可进行生活习惯的改变,疾病的积极干预来降低子宫内膜病变的发生风险。
文章编号:1003-6946(2015)07-495-03
子宫内膜癌及癌前病变第4版
WHO的分类解读
沈丹华
(医院病理科,北京100044)
中图分类号:R737.33文献标志码:B
子宫内膜癌在西方国家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肥胖及代谢性疾病的增加,子宫内膜癌的发病率也呈逐年增高的趋势,已经成为女性生殖系统第二大常见恶性肿瘤。众所周知,子宫内膜癌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肿瘤,它是由生物学和组织学各异的一组肿瘤组成,包括了不同的组织学类型,每一型都具有其独特的病理学表现以及不同的生物学行为。依据子宫内膜癌发病机制的不同可将其分为两大类:即Ⅰ型和Ⅱ型子宫内膜癌。准确的病理诊断对于临床精准的个体化治疗,提高患者生存率处理至关重要。随着对子宫内膜癌发病机制及分子遗传学改变的认识,对子宫内膜癌的分类方式以及命名也有所变化,第4版WHO女性生殖器官肿瘤分类(以下简称为第4版WHO分类)2014年刚刚出版,其中对于子宫内膜上皮性肿瘤及前期病变的分类及命名做了一些修订,妇产科临床医生应该正确认识和理解这些变化以及临床意义,本文将结合相关内容及近年的新进展做简单介绍。
1 Ⅰ型子宫内膜癌与癌前病变
Ⅰ型子宫内膜癌中最为常见且最典型的病理类型是子宫内膜样癌,分化好的子宫内膜样癌的腺体成分类似于高度增生期的子宫内膜腺体,因而得名。这型肿瘤与雌激素密切相关,属于雌激素依赖性肿瘤。常见于生育期及围绝经期妇女,病变前期常常出现子宫内膜增厚,不规则阴道流血等子宫内膜增生性表现,其明确的癌前期病变是子宫内膜的不典型增生。有关子宫内膜增生症以及Ⅰ型子宫内膜样癌前期病变的病理学分型及命名不断变化与更新,1994年版以及2003年版的WHO女性生殖道肿瘤分类中,有关子宫内膜增生症均采用的是Kurman和Norris提出的分类方法,这一分类法依据子宫内膜腺体的结构复杂及拥挤程度先分为“单纯性增生”和“复杂性增生”,再根据腺上皮细胞核是否出现异型性,再分为“不伴典型性的增生”和“不典型性增生”[1]。医院,甚至还将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再分成轻度、中度及重度。然而,实际应用过程中,发现在病理分型或分级中,越细致,其诊断重复性越差,而这样的区分与临床实际处理及患者的预后关系并不大。在2014年新出版的第4版WHO女性生殖系统肿瘤分类中,有关子宫内膜增生性病变取消了单纯性及复杂性之分,将子宫内膜增生性病变原来的四型简化为两大类:不伴有不典型性的增生(hyperplasia without atypia)与不典型性增生(atypical hyperplasia,AH),之所以取消了单纯性增生与复杂性增生之分,是因为在临床预后及处理上,单纯性增生与复杂性增生间的差别不大,而是否具有细胞及结构的不典型性是临床预后的关键。因此,两级分类法在病理诊断中更具可重复性,诊断者之间的一致率(Kappa值)提高。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版分类中将AH与子宫内膜样上皮内瘤变(endemetrioid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EIN)并列命名为:AH/EIN[2]。EIN是在2000年由Mutter及其国际子宫内膜合作组提出的一种分类方法,这一分类除了北京白癜风断根治疗的医院北京医院白癜风治疗
转载请注明:http://www.oohkt.com/wazlyy/9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