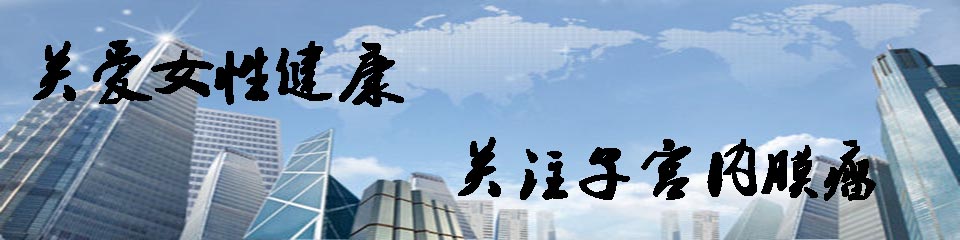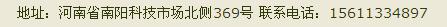非常翻译从非典型增生性肿瘤和非侵袭性
摘要:卵巢浆液性交界性肿瘤(SBT)的话题一直相当有争议,特别是在术语和行为方面。有人认为在结构上具有异质性,其中大部分是典型的良性疾病被称为“非典型增生性浆液性肿瘤(APST)”,还有一小部分具有微乳头结构,预后差,被称为“非侵袭性低级别浆液性癌(niLGSC)”。也有人认为,这两组之间的行为差异不是基于原发肿瘤的亚型,而是由于卵巢外疾病的存在,特别是浸润性种植。根据WHO术语,典型的SBT等同于APST,具有微乳头结构的SBT等同于niLGSC。此外,“浸润性种植”被重新命名为“低级别浆液性癌”(LGSC)。至于究竟是原发性肿瘤还是卵巢外LGSC的存在主导了患者预后,依然众口不一。本研究始于年,旨在确定预后的预测因素,并重点研究原发性肿瘤的病理外观(APSTvs.niLGSC)和卵巢外疾病(非浸润性/浸润性种植)。该研究以人口为基础,涉及丹麦所有的女性人口。本研究失访率为零,最长随访时间达36年(中位随访时间15年)。所有病理切片都由2名病理学家(R.V,和R.J.K.)在对随访双盲的情况下重新审查。在排除非SBT患者,患有其他癌症,具有癌症病史及癌症阶段不明确的患者后,共纳入例,其中APST组名,niLGSC组75名。患者中位年龄为50岁(16-97岁)。名患者(86%)表现为FIGOI期疾病,名患者(14%)患有晚期疾病。与APST相比,niLGSC组发生双侧发病、术后残留肉眼可见病灶、微浸润/微浸润癌、晚期疾病和浸润性种植的频率明显较高(p<0.)。由于死亡证明中很难准确判定死因,作者将疾病继发侵袭性浆液性癌作为癌症发展的主要终点,死亡率非常高。在整个队列中,继发癌症发生率为4%,其中93%为低级别,7%为高级别(距离初诊中位时间为10年;最长为25年)。在根据APST或niLGSC诊断时的年龄和诊断后的时间进行调整后,在所有分期组合中,niLGSC的癌症发生率明显高于APST(危险比[HR]=3.8;95%置信区间[CI],1.7-8.2)。这种差异在I期病例显著,但在晚期病例中并不显著。此外,APST和niLGSC的全因死亡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所有患有晚期疾病的妇女中,例(86%)合并非浸润性种植,而19例(14%)合并浸润性种植。非浸润性种植与继发癌症显著相关(HR=7.7;95%CI,3.9-15.0),但浸润性种植的风险明显更高(HR=42.3;95%CI,16.1-.1)。总之,尽管浸润性种植是预测不良结果的最重要特征,但是对APST和niLGSC进行细分仍然很重要,因为两者在晚期疾病和浸润性种植的风险以及I期疾病继发浆液性癌的风险上不同。(AmJSurgPathol;41:–)
关键词:浆液性交界性肿,微乳头变异,非典型增生性浆液性肿瘤,非侵袭性低级别浆液性癌,非侵袭性微乳头浆液性癌,低度恶性浆液性肿瘤
对卵巢浆液性交界性肿瘤(SBTs)的认识,自20世纪70年代初起始,SBTs在FIGO、WHO卵巢肿瘤分类中被确立为一个独特的组别后,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一是浸润性种植是预测不良结局的重要因素,其二是病理呈微乳头状或筛孔状的SBTs更多地与浸润性种植和浸润性行为相关。后者提示典型的SBT为良性病变,而微乳头状的SBTs是一种非侵袭性的低级别浆液性癌(niLGSC)。因此,前者被称为“非典型增生性浆液性肿瘤(APST)”,后者被称为“非侵袭性低级别浆液性癌”,这为整组肿瘤的“低恶性潜能”行为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解释。但随后的多项研究对典型SBT和微乳头状变异疾病的临床病理特征进行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其中有人提出niLGSC相关的不良预后不是由于本身的卵巢癌表征,而是由于相关的浸润性种植导致,该结论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论。根据年WHO分类的术语,典型的SBT等同于APST,显示微乳头结构的SBT等同于niLGSC。此外,“浸润性种植”被重新命名为“低级别浆液性癌”。但是关于究竟是原发性肿瘤,还是卵巢外LGSC决定了疾病预后的争论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回顾先前发表的关于SBT的研究,可发现多数研究具有较大局限性,不利于对SBTs行为的准确理解。如相对较少的个案(<例)、相对较短的随访时间(8y)、大量的失访病例,以及选择性偏倚。最后,少数基于人群的研究要么缺乏病理再分析,要么患者数量相对较少或随访时间较短。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基于人群的非侵袭性低级别浆液性肿瘤研究,涉及丹麦全体女性人口。研究包括病理再分析和长期随访,并且失访率为零。目前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描述APST和niLGSC,以及种植和微浸润/微浸润癌的临床病理特征,并评估APSTs和niLGSC与非浸润性和浸润性种植体之间的行为差异。研究排除了有癌症病史的女性(除非黑色素瘤皮肤癌外的卵巢或非卵巢部位肿瘤)。
研究方法研究人群这项研究得到了丹麦数据保护局和丹麦科学道德委员会的批准。本次纳入研究的丹麦人群的完整流行病学特征和研究设计细节在先前已有报道。简而言之,研究纳入了丹麦全国在年至2年期间在丹麦病理学数据库和/或丹麦癌症登记处进行鉴定的SBT病例。在共计例纳入病例中检索了例病理切片,在重新审查这些HE染色切片后,排除了例非SBT患者。其中伴有微小/局灶性上皮增生的浆液性囊腺瘤/腺纤维瘤例,交界性非浆液性肿瘤12例,其他浸润性肿瘤16例。同时为检测被错误归类为癌症的SBT,检索了从年到2年诊断为高分化浆液性癌的病例,在共例此类病例中计48例在病理审查后被重新诊断为SBT。最终诊断为SBT的共计例病例。在所有的分析中,我们排除了在诊断SBT之前或同时有癌症病史(除非黑色素瘤皮肤癌外的卵巢或非卵巢部位肿瘤)的女性,以及未确定SBT分期的女性,最终纳入SBT患者数目为名。
病理学再审查所有来自原发性卵巢肿瘤和非卵巢部位的HE染色切片均取自丹麦各病理科。所有切片由两位作者(R.V和R.J.K.)盲法进行再审查,。根据2年和年WHO研讨会的标准对SBT进行了分类。SBT被定义为一种非侵袭性的低级别浆液性肿瘤,向囊内或外生性生长,具有沿上皮分层排列的乳头状结构,在结构上表现出比囊腺瘤/腺纤维瘤更强的增生性,但缺乏浸润性癌的破坏性间质浸润。诊断为SBTs需要至少10%的有别于乳头状浆液性囊腺瘤/腺纤维瘤的肿瘤上皮增生。
肿瘤亚分类为APST或niLGSC。微乳头聚集生长最大直径≥5mm的肿瘤为niLGSC,未见微乳头聚集或微乳头病灶生长最大直径<5mm的肿瘤为APST。必须强调的是,在诊断niLGSC时,应考虑细胞学特征。不同于常由异质性的立方、柱状、纤毛和圆形细胞组成的APSTs病灶,niLGSC病灶细胞外观相对一致,具有较高的核质比,较粗的核染色质,并常见小而突出的核仁,非常类似浸润性LGSC。此外,它们缺乏APST中明显的嗜酸性细胞和纤毛细胞。
根据传统(组织浸润)及扩展标准将种植分为非浸润性(上皮性或促纤维增生性)及浸润性两种。后者适用于种植显示与niLGSC相似的微乳头状或筛状/聚集形态和/或病灶呈实心巢状,周围有明显间隙且未明显浸润正常基底组织。
由于不同研究中区分”微浸润”上限和浸润性LGSC下限的阈值不同,而且没有建立科学有效的测量方法,因此只要病灶没有出现破坏性间质浸润,便不采用特定的尺寸界限将其分组。因此,无论病灶大小或数量如何,间质浸润模式均未显示破坏性的间质浸润。所有病例均按照最大病灶直径<3mm、≥3ー5mm、≥5mm区分。
年WHO妇科肿瘤分类描述了两种类型的“微浸润”。其中常规型较常见,表现为基质内的单个细胞,小细胞群或小乳头凸起,这被称为“微浸润”。另一种较不常见的类型以微乳头为特征,此外还常含有周围有明显空间或间隙的实心细胞巢,以及倒置的巨乳头状和筛状病灶,因类似侵袭性LGSC而被称为“微浸润癌”。本次研究中,病例被分类为常规型微浸润或微浸润癌(无论是否有并存的常规类型微浸润)。
手术及分期纳入患者接受医院是通过与丹麦国家病人登记处联系来确定的。对所有的医疗记录进行了审查及数据提取。所有患者均按照丹麦的卵巢交界性肿瘤/癌症临床指南进行治疗,先前该指南不一定包括完整的分期和淋巴结清扫。鉴于组中少量淋巴结数据的缺失,无法得出淋巴结受累的影响。但是,SBT中淋巴结受累通常不被视为不利的预后因素,因此,缺乏淋巴结数据不太可能影响生存分析。肿瘤分期采用年前的FIGO分期系统,并根据从医疗记录以及卵巢外组织病理切片再审查确定。
随访以APST形式复发的肿瘤被归类为“疾病复发”,以期与继发的浆液性癌分开归类。本研究直到年8月31日与丹麦病理学数据库对接。所有患者从初步诊断为SBT后6个月开始在病理数据库中进行随访。所有的病理记录及HE切片(复发/继发浆液性癌)都被保存,包括与原发肿瘤切片和最初手术时的种植物切片的附加比较。继发的浆液性癌根据年WHO的标准进行分类。
我们没有研究疾病特异性生存率,因为非侵袭性低级别浆液性肿瘤往往呈惰性进展,并在多年后复发,这将混淆确切的死亡原因。而死亡证明书常常在没有证据表明死亡时有肿瘤存在的情况下仍将死亡原因列为“卵巢癌”。因此,考虑到已知的不良结果,研究将组织学证实的继发性浸润性浆液性癌的发生作为主要终点替代疾病特异性生存期。这同时也是因为被诊断为非侵袭性低级别浆液性肿瘤的患者可能死于肿瘤进展或与非恶性并发症有关的死亡(例如种植导致的粘连,这是非侵袭性低级浆液性肿瘤常见的并发症),研究也提供了全因死亡率来比较APST与niLGSC患者在预期寿命上的差异。
统计分析X2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用于比较分类变量,t检验用于比较连续变量。分别计算从原发性卵巢肿瘤(APST或niLGSC)诊断时至继发性侵袭性浆液性癌发生及全因死亡的时间。Cox比例风险模型用于分别评估卵巢肿瘤类型和种植类型两者与继发浆液性癌和全因死亡率之间的关联。关联性用危险比(HRs)和95%置信区间(95%CIs)表示。所有统计都将年龄视为连续的协变量。统计建模使用SAS/STAT8.2版(SAS研究所,NC)。
结果一般临床病理特征研究共纳入例APST及niLGSC患者进入随访。其中,名女性(92%)仅患有APST,而75名女性(8%)仅患有niLGSC。21名女性(28%)患有对侧的APST。与APST相比,niLGSC与双侧发病(45/75[60%]vs./[34%];p<0.)、微浸润/微浸润癌(7/75[9%]vs.18/[2%];p=0.)及术后残留肉眼可见病灶(12/75[16%]vs.42/[5%];p<0.)有显著相关性。两种肿瘤类型在年龄、肿瘤大小、卵巢表面受累及子宫内膜异位症发生率方面没有显著差异(表1)。
原发卵巢肿瘤的组织学特征APST肿瘤平均组织取样水平为1.1块/cm(范围,0.1-11.3),26例缺乏取样信息。肿瘤为囊内和/或外生型(伴或不伴自体种植),表现典型的APST特征,具有分级乳头状分支,较大的乳头逐渐分支成较小的乳头分支,终止于小乳头状细胞簇(图1)。乳突由异质性的立方、柱状和圆形细胞排列组成,细胞内有丰富的嗜酸性胞浆。常见纤毛,细胞核染色较浅。偶可见沙粒体。图1APST.(A和B)大乳突逐级分支成较小的乳头,最终止于分离的小上皮簇(B和C)。其他区域呈乳头状腺纤维瘤样改变(D)。A-D都来自同一个病例。计有40名女性(5%)病灶微乳头直径测量≥1mm但<5mm,因此,不符合niLGSC的诊断标准。其余名患者(95%)病灶不含有微乳头成分。
名女性(27%)肿瘤的结构主要是囊腺瘤/腺纤维瘤,其中APST成分占肿瘤<50%,大部分为浆液性囊腺瘤/腺纤维瘤成分(图1D)。其余73%的病例不含囊腺瘤/腺纤维瘤成分,或者囊腺瘤/腺纤维瘤成分占比小于肿瘤的50%。
niLGSC
肿瘤平均组织取样水平为1.5块/cm(范围,0.3-7.7),3例缺乏取样信息。肿瘤为囊内和/或外生型(伴或不伴自体种植),表现典型niLGSC特征(图2)。一般来说,niLGSC缺乏典型的APST分级乳头状分支模式。相反,较大的乳突通常立即转变为细长的微乳头状结构,其长度通常是宽度的5倍。通常,在较大的乳突之间可见片状脱落的微乳突。并可见数量不等的筛状结构(图3)。偶见沙粒体。
图2niLGSCA:大的圆形乳突周围直接从较大的乳突发出的拉长微乳突,没有典型的APST分级分支模式(美杜莎外观)。B:在较大的乳突之间紧密排列的微乳突。C:其低级别细胞学特征与侵袭性LGSC相似。A-C都来自同一个案例。可将细胞学特征与图1中的APST进行对比。图3niLGSC病灶的筛状结构部分肿瘤为单纯niLGSC,其余病灶位于APST背景中。所有病例均符合niLGSC的诊断标准,及微乳头结构最大直径≥5mm,微乳头占比因病例而异(中位数70%;平均值60%;范围,1%至%)。11名患者(15%)肿瘤的结构主要是囊腺瘤/腺纤维瘤,其中niLGSC成分占肿瘤<50%。另外85%的病例没有囊腺瘤/腺纤维瘤成分或者囊腺瘤/腺纤维瘤成分占肿瘤大于50%。FIGO分期APST的分期分布如下I期例(87%),II期54例(6%),III期59例(7%)。niLGSC的对应分布为:I期55例(73%),II期11例(15%),III期8例(11%),IV期1例(1%)。niLGSC病例更频繁地表现为高分期(表2)。
卵巢外种植
晚期APST患者中,例(92%)发现有非浸润性种植(图4),而9例(8%)发现了浸润性种植。对于晚期niLGSC,计10例(50%)非浸润性种植,10例(50%)浸润性种植(图5)。niLGSC与浸润性种植的频率明显增高有关(表2)。
图4非浸润性种植A由上皮细胞排列成的中等尺寸的乳头形成的种植,其外观与卵巢APST相似。B、C、促纤维增生型种植体,有丰富的促纤维增生性基质和相对缺乏的上皮结构。图5侵袭性种植A下层正常组织浸润B不伴下层正常组织浸润,类似于卵巢niLGSC的外生型微乳头模式(按照扩展标准)C不伴下层正常组织浸润,位于透明的腔隙内有细胞和微乳突的实心巢(按照扩展标准)。微浸润/微浸润癌18例APST伴有微浸润/微浸润癌患者中,10例(10/18;56%)仅有常规类型的微浸润(图6),8例(8/18;44%)为微浸润癌(表3)。病灶数量从1个到多个不等;单个病灶的最大直径:15名女性<3mm,1名女性为3-5mm,2名患者中≥5mm。但两种类型均未见破坏性间质浸润。
图6常规类型微浸润。由个体或小团细胞组成,基质内可见大量嗜酸性物资,细胞核染色较浅
7例niLGSC患者(7/75;9%)患有微浸润癌(图7),其中1例(1/7;14%)同时合并常规类型的微浸润(表4)。7名女性无一人仅存在常规类型的微浸润。病灶数量从1个多个不等;病灶最大直径:2名女性为<3mm,3名女性为3-<5mm,2名患者中≥5mm。两种类型均未见破坏性间质浸润。其中1例病灶呈“倒置的巨乳头状”型(图8),2例为筛状型。
图7微浸润癌。基质内透明间隙内的小乳突。注意圆形细胞核的相对均匀的细胞群,细胞多见突出的小核仁,与图6所示的常规类型的微浸润相比,核质比较高。图8微浸润癌合并巨乳头结构。比图7中更大的乳突出现在基质的透明间隙内。乳头状突起具有丰富的纤维性基质核心,其特征与侵袭性LGSC中的倒置巨乳头结构基本相同,因而被包括在微浸润癌的范围内。关于微浸润/微浸润癌,APST中单纯常规型微浸润的发生率高于niLGSC(10/18[56%]vs.0/7[0%]),而niLGSC中微浸润癌的发生率高于APST(7/7[%]vs.8/18[44%])(p=0.02)。此外,微浸润癌与晚期疾病的相关性高于单纯微浸润型(7/15[47%]vs.2/10[20%]),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APST组中,随访期间,10例(10%)患者仅发生常规类型的微浸润,8例(25%)患者继发了浆液性癌。在niLGSC中,7例(0%)微浸润癌中无一例发生癌变。由于病例数量少,无法进一步分析单纯传统类型微浸润与微浸润性癌的关系。APST/niLGSC与继发浆液性癌及死亡相关风险本研究无1例患者失访,随访时间最长达36年(中位随访时间为15年)。41名APST或niLGSC患者(4%)继发了浸润性浆液性癌,其中38例为低级别,3例为高级别。诊断APST/niLGSC至继发浆液性癌的中位时间为10年(范围0.6-25年)。其中APST组为33名患者(4%),niLGSC组为8名(11%)(图9)。在调整诊断APST或niLGSC后的年龄和时间后,niLGSC继发浆液性癌的风险显著高于APST(HR:3.8;95%CI,1.7-8.2)。但以全因死亡率作为另一个终点时,调整年龄及诊断APST或niLGSC的时间后,niLGSC患者的死亡风险与APST组没有显著差异(HR:1.2;95%CI,0.8-1.9)(表5)。
图9继发的浆液性癌。A:原发性卵巢肿瘤(niLGSC)。B:8年后的侵袭性LGSC。注意非侵袭性和侵袭性肿瘤的形态学相似性。种植及类型与继发浆液性癌及死亡相关风险无论是APST还是niLGSC中,非浸润种植/浸润性种植与无种植物相比,均显著增加了浆液性癌的继发概率(非浸润性种植与未种植相比:HR,7.7;95%CI,3.9-15.0;浸润性种植与无种植相比:HR,42.3;95%CI,16.1-.1,)(表5),且浸润性种植风险更高。当直接比较浸润性种植与非浸润性种植时,浸润性种植与继发浆液性癌的风险显著相关(HR=9.0;95%CI,2.5-32.7)(表6)。此外在对诊断APST/niLGSC的年龄和距离时间进行调整后,非浸润性/浸润性种植与全因死亡率显著相关:非浸润性种植相对于I期疾病(HR=1.8;95%CI,1.3-2.6);浸润性种植相对于I期疾病(HR=6.6;95%CI,3.7-11.8)(表5)。
APST/niLGSC、种植的存在/类型与继发浆液性癌及死亡的相关风险对于没有疾病种植的患者,例APST患者有13名(2%)继发浆液性癌,而niLGSC中,继发癌症比例更高(4/55[7%])。而在发现种植的女性中,APST和niLGSC之间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对于非浸润性种植,名APST患者有17名(16%)继发了浆液性癌,在10例niLGSC中为1例(10%)继发;对于浸润性种植而言:9位APST患者计3位(33%),10名niLGSC计3位(30%)继发性浆液性癌。
经过对诊断APST/niLGSC的年龄和距离时间进行调整后,在不伴疾病种植的患者中,与APST患者相比,niLGSC患者继发浆液性癌的风险显著增加(HR=5.4;95%CI,1.8-16.9)。在调整了微浸润癌(有/无)后差异仍具有统计学意义(HR=6.2;95%CI,2.0-19.3)(表6)。然而全因死亡相关风险未见差异(HR=1.1;95%CI,0.7-1.8)(表6)。而在发生种植的患者中,调整年龄、距诊断时间以及种植类型后,继发癌症风险与APST、niLGSC与种植类型均无显著相关性(表6)。即使调整微浸润癌这一因素后差异也没有统计学意义(HR=0.5;95%CI,0.1-2.5)(表6)。相比之下,在调整年龄、诊断时间和卵巢肿瘤类型(APST或niLGSC)后,种植类型是继发浆液性癌的一个重要的预测因子(HR=9.0;95%CI,2.5-32.7)。对微浸润癌进行调整后,差异仍具有统计学意义(HR=6.9;95%CI,1.6-30.5)(表6)。在全因死亡相关风险方面也观测到类似的结论,只是并非如此明显(表6)。
讨论研究分析了总队列关于继发浆液性癌的相关风险,并确定了复发和进展的风险因素。在目前以人口为基础的长期研究中,我们发现APST/niLGSC呈现高度惰性,而且I期niLGSC患者发生继发性浆液性癌的风险明显高于APST患者(表5和表6)。即使控制了表面受累因素(如IC期疾病),I期niLGSC组与继发浆液性癌的关系依然显著,然而,APST和niLGSC的总死亡风险(全因死亡率)在I期或高于I期的病例中是相似的(表6),这表明除了癌症的发展,其他因素也可能导致预后不良结果(例如,非浸润性种植粘连导致的小肠梗阻等)。这些发现在以前的研究中没有被观察到。然而,出于多种因素,解释其他研究的结论数据并不轻松。这些问题包括外科治疗的差异(保守/保留生育能力的手术与完整性不尽相同的分期手术),缺乏统一的病理学审查,浸润性种植的标准不同,病例数量少,选择性偏倚,随访时间短,患者失访,以及在比较APST和niLGSC时没有考虑人-年关系。
研究的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尽管I期niLGSC与I期APST相比在继发癌症的风险上明显更高,但是在晚期的niLGSC和晚期APST中没有这种风险的差别。一般来说,尽管不如浸润性种植的风险高,但伴有非浸润性种植的晚期非侵袭性低级别浆液性肿瘤与I期非侵袭性低级别浆液性肿瘤相比后续继发浆液性癌风险是显著增高的。更具体地说,在我们之前对该队列的一项流行病学研究中,即使是非浸润性种植的APST,与I期APST相比,继发浆液性癌的风险也明显更高。因此对于晚期疾病的情况下,种植的存在(即使是非浸润性)是极重要的不良预后因素,其重要性甚至过了卵巢肿瘤的组织学类型。
在我们的研究中,21%提交给病理小组的SBT标本不符合诊断,最常见的是因为他们是主要成分为浆液性囊腺瘤/腺纤维瘤,上皮类增生只占肿瘤<10%。余下小部分病例则是其他类型肿瘤被误认为SBT。虽然结构/定量特征可以区分APST和niLGSC,但是必须
转载请注明:http://www.oohkt.com/wadzz/105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