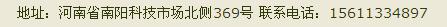列维middot斯特劳斯我们都是食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evi-Strauss,公元年月28日—公元年0月30日),法国作家、哲学家、人类学家,结构主义人类学创始人和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区,逝世于法国巴黎,享年00岁。生前曾出访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日本和朝鲜等国,被认为是“所有流派(和无流派)思想者的财富”,被国际人类学界公认的最有权威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类亲属关系、古代神话以及原始人类思维本质三大方面,他把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研究纳入自己的神话研究当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结构主义神话学。青年时代爱好哲学,醉心于卢梭、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思想。20世纪30年代他曾在巴西考察当地土著社会多年。20世纪40年代旅美期间钻研英美人类学与结构语言学,陆续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并在期间与布拉格学派创始人雅各布森在纽约邂逅。20世纪50年代后与萨特激烈辩论,并在期间任法兰西学院教授。年74岁时退休,但仍致力于在实验室里研究人类学直至逝世。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列维-斯特劳斯是他的姓,他与马凌诺斯基(BronislawMalinowski,—)并称为结构功能主义之父,曾被和梅洛-庞蒂和布尔迪厄联系到一起。
社会问题:割礼和人工生殖
Problèmesdesociété:excisionetprocréationassistée出自“Ilsegretodelledonne”,LaRepubblica,4novembre选自《我们都是食人族》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数十年来,人类学家和他们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已有显著改变。从前被当作殖民地的国家,现在已然独立,它们抱怨人类学家鼓励旧习俗和过时的信仰,阻碍它们发展经济。对急于现代化的民族而言,人类学家就像殖民主义的最后化身,它们不信任他,甚至表现出对他的敌意。
此外,有一些少数原住民,继续在一些大型的现代国家如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巴西等地生活。这些原住民对于自身的民族性格、道德和法律权利都有比较深层的认识,拒绝被人类学家作为研究对象,他们将人类学家视为知识领域中的寄生者,甚至剥削者。随着工业文明的扩张,能够保持传统生活方式并作为人类学家研究对象的社会,数量已显著下降。与此同时,“二战”以后,因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流行,研究人员的数量倍增。在美国,五十年前已有人开玩笑地说,印第安家庭成员至少包含三个人:丈夫、妻子和人类学家……自此,情势每况愈下,原住民群体厌倦作为人类学家的猎物,开始反抗。要进入他们的保留区,人类学家有时需要满足他们各式各样的要求。其他的则是纯粹禁止人类学研究:我们可以以教师或医护人员的身份进入他们的居所,但必须提供一份书面承诺,不准询问有关社会组织或宗教信仰的任何问题。受访者非必要时不会讲述神话,除非签署合同,而合同中必须承认他拥有作品的所有权。
但是,由于事态的反转,人类学家和他所研究的民族之间的关系,有时也会随之反转。部落求助于人类学家,甚至雇用他们,请他们出席法庭,协助维护原住民的土地权利,废除曾经强加给他们的规约。例如在澳大利亚,原住民和人类学家曾多次试图阻止政府在原住民的圣地设置火箭发射场或给予采矿特许。这些诉讼涉及的所有权相关地区有时无边无际。加拿大和美国也都持续进行同类型的诉讼。在巴西,印第安人开始筹划组成全国性的组织,可以预见的是,他们也会发起类似的行动。在这些情况下,人类学家的工作性质完全改变了。以前人类学家雇用当地原住民,现在则是原住民雇用人类学家。诗歌中颂扬的冒险让位给了图书馆中严肃生硬的研究,伏案累牍的档案整理,用以丰富事件的数据,并以合法的方式将之统合。官僚主义、程序步骤取代了生动的“田野调查”,或者至少改变了田野调查的精神。
*
法国人类学家从未思及会在自己的国家遭遇相同的经历,然而由于移民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特别是来自非洲大陆的移民),这一情形正在发生。近一两年来,许多律师求助于人类学家,一起为非洲移民辩护,因为他们亲自或请专业人士为他们的女儿执行割礼。女权组织以及其他致力于保护孩童的团体则在由检察署提起的诉讼中担任原告。最初,女性割礼被视为轻罪,由地方法院审理;但自年起,根据法国法律,割礼被认定为故意袭击与伤害,改由重罪法院审理,而父母为孩童实施割礼也被认为是有罪的。
年的一起案例判决引发了争议,因为女孩已经死了——似乎不是因为割礼本身,而是因为忽略了割礼的后遗症。因此,检方除了袭击和伤害外,还提出了危险时无人援助的控告。年0月初,巴黎重罪法院裁定另外一起女性割礼案件,此案件中女孩没有因为割礼而受到任何伤害。但是这两起案例宣告的惩处是完全一样的:三年缓刑……没有什么更能显现法庭的尴尬了:无论执行割礼的结果如何,致命或无害,法庭全都觉得必须同时给予谴责和宽恕。
非洲和印度尼西亚的许多民族有女性割礼的习俗(古埃及时期已经存在),切除阴蒂之外,有时也会切除小阴唇。未接受割礼的女孩被认为是不纯洁,甚至是危险的,将无法找到结婚对象。与欧洲人的普遍认知相反,这种做法并非由于受到男性强迫;年的诉讼案中,被告的口译员解释:它是“女性间的秘密”。女人们都希望女儿与自己一样,接受割礼。
在提起诉讼之时,检察署同时受到女权主义团体和其他协会所把持的公众舆论的压力。这些组织如何为他们的愤怒辩解呢?
首要的起诉理由似乎是:割礼使女性不再拥有快感,而这是我们社会宣扬的人权之一。第二个起诉理由是:女性割礼是对孩童身体的伤害。
令人惊讶的是,后一种说法,从来不曾也一直未被提出来反对男性割礼——这两种侵犯属于同一类型。有些人认为,男性割礼是温和的小手术,不像女性割礼可能导致被诟病的严重缺陷。然而这种观念对或错?我有位好朋友,来自布勒托讷旧式的天主教家庭,他深信割礼会减损男性的快感,因此不想妥协。关于女性割礼的看法则见仁见智。对于女性的敏感带,我们的认识如此模糊,因此最好承认我们所知极少。在年0月的诉讼中,我们听到一位接受过割礼的非洲女医师宣称她从未感觉在这方面有所匮乏。她补充说,她来到巴黎后才知道,受过割礼的妇女会性冷淡……
无论如何,显而易见的是,即使对快感没有任何影响,男性割礼依旧损害了孩童的身体,使得孩子自觉与其他孩子不同,就像女性割礼一样。我们不明白,后者所引起的议论为何在男性割礼上却不复见;是否仅仅因为我们太过熟悉于犹太—基督教文化,才使得我们对男性割礼应带来的震撼免疫。男性割礼属于一个共同的文化遗产,对犹太人而言是直接的,对基督徒则是间接的。因此(而且也仅仅因此)它不会令我们困扰。
在关于女性割礼的诉讼中,辩护律师请教人类学家的意见在两个辩护路线之间进行选择。他们相信,并且认为可以说服法官,在这些被视为落后的社会中,个体并没有自由意志,他们完全受制于团体所施予的约束,因此不必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关于这点,人类学家与律师的观点不同。他们知道,对于那些被误称为原始或古代的社会而言,这种想象是属于9世纪的过时思想。在所有社会中,包括那些被误判的社会,个体行为存在很大的不同。虽然其成员或多或少会忠于群体规范,然而并非绝对无法逃脱。因此,这样的辩护方式,律师或许会为他的客户得到赦免的机会,但同时会使他们和他们的文化丧失信誉。矛盾的是,辩护人却因此强调了原告的良知,因为他们也同意原告所代表的文明绝对至上性,并且法院还能依此宣判。
而人类学家则试图让法官了解,即使我们认为割礼是野蛮和荒谬的,但赞同这些信念的人应是无罪的。在拥有女性割礼或男性割礼习俗的地方(这两个习俗往往是并存的),两者有共同的潜在逻辑:造物主在确立两性之间的区别时并没有善尽职责。因为工作时太急躁、太粗心或者受到干扰,他在女人身上留下一丝阳刚之气,男人身上又带有一点女性魅力。阴蒂、包皮的去除,是为了使作品尽善尽美,摆脱性别原有的残余杂质,让两性都能合乎它们各自的性质。这种形而上的思维与我们不同,但我们仍然可以认同其一致性,而非无视它的美丽与壮阔。
因此,与其将被告视为下等阶层,并不知不觉地呼应了种族主义者的偏见,人们应努力证明的是,在某些文化情结中无意义的习惯在另一文化可能意义非凡。因为,并没有一个共同标准足以评断任何信仰体系,更谈不上可因此对某个体系加以谴责;除非认为其中一种信仰(当然,就是我们的)代表了普世价值,而且可以成为举世所依。但,我们基于什么理由可以如此认为?
没有任何人能以特定道德之名来惩罚别人,他们只是遵循自己原有的道德伦理习惯。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顺应这些不同习俗?结论并非显而易见。人类学家、伦理学家的客观观察显示,在我国,女性割礼会引起公众良心上的抗拒。我们的价值体系,和其他价值体系一样,有权受到尊重。如果在同一块土地上,无法兼容的两种习俗可以自由地融为一体,我们的价值体系将因此深受伤害。因此,女性割礼的审判具有示范价值。虽说认为可以对该行为加以谴责的想法是荒谬的,但倘若一个道德选择涉及了当地文化的未来,只可能有两种方向:若非表明所有习俗在任何地方都是被容许的,便是将那些打算继续忠实于他们习俗的人遣返回他们的祖国(尽管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无论动机为何,他们严重伤害了接待国的感情)。
在年和年的判例里,于被告眼中,唯一的解决之道是,比起驱逐出境,缓刑可能是一个较为宽松的处罚。
*
在另一个领域,人类学家同样被推上公共舞台。许多国家邀请人类学家加入政府的咨询委员会,就有关人工生殖的新方法提供意见。因为面对生物科学的进步,舆论一直摇摆不定。对于患有不孕症的夫妇(无论是一方或双方),有几种方法可以拥有孩子:人工授精,卵子捐赠,租借子宫,与来自丈夫或另一名男子的精子或是来自妻子或其他女人的卵子进行体外受精。这所有的方式都该被允许吗?或者应该允许某些方法,而排除其他的?然而,又该根据什么标准判定?
欧洲国家的法律对于这种司法上前所未有的情形,没有现成的答案。当代社会认为,亲子关系是来自生物学上的联结(比起认为那是一种社会性联结的看法似乎更具优势),英国法律甚至不存在社会性亲缘关系的概念。根据这种概念,精子捐献者可以依法要求拥有孩子,或者可以依需求保留这样的权利。在法国,拿破仑法典规定,母亲的丈夫是孩子的法定父亲,它否认生物性亲缘关系,而独厚社会性亲缘关系。法国的古老格言说:父亲,即是婚姻关系所指定之人(Pateridestquemnuptiaedemonstrant)。然而,年的一条律法违背了此精神,因为它允许追寻亲子关系。我们不再知道社会性或生物性何者优先于另一者。那么,对于人工生殖所带来的问题:法定父亲并未提供精子,而且母亲本身没有提供卵子,也未提供妊娠时所需的子宫,我们该如何判断?
由此一过程所生育的孩子,根据不同情况,有一位父亲和一位母亲是正常的,也可能有一位母亲和两位父亲、两位母亲一位父亲、两位母亲两位父亲、三位母亲一位父亲;如果提供精子者和丈夫不是同一人,过程中又涉及了三个女人:一者提供卵子,一者出借子宫,而第三者将是孩子的法定母亲,孩子甚至会有三位母亲和两位父亲。
社会性父母和生物学上的父母自此不再合一,那么该如何判断他们的权利和义务?若提供子宫者孕育出畸形的孩子,而这对夫妻请求法庭协助,拒绝接受这样的小孩,法庭该如何解决这样的难题?或者,相反,如果一名受托于不孕夫妇,接受男方的精子而受孕的女子,改变主意想要保留这个孩子,法庭又该如何面对?对于所有的要求,例如,一名女子要求与她已故丈夫的冷冻精子进行人工授精;两位女同性恋希望以其中一人的卵子,通过人工方式接受匿名捐赠而受精,再将受精卵移植到另一个人的子宫内,以得到一个孩子,是否都应该视为合法正当?
精子或卵子的捐赠、子宫的出借,是否也可以成为有偿契约的对象?捐赠者应该匿名吗?或者社会性父母以及孩子自己,也可以知道生物学上双亲的身份?这些问题并非毫无根据,它们和其他更加匪夷所思的问题都已持续发生。所有这一切都前所未闻,法官、立法者,甚至伦理学家都缺乏类似的经验,完全束手无策。
但并非只有人类学家不会受到此类问题的困惑。当然,他们所研究的社会,对于体外受精、卵子或胚胎的提取,然后转移、植入和冷冻的现代技术一无所知,但这些社会已经设想过隐喻上相等的情况。因为它们相信其现实性,所以在心理和律法方面同样也都做过构想。
我的同事埃里捷-奥热(Héritier-Augé)女士曾经指出,在非洲布基纳法索的萨莫人(Samo)有类似捐赠授精的行为。在那里,女孩年纪很轻就结婚。而在前往她的配偶处生活之前,每个女孩都必须拥有一名正式恋人。一旦时机成熟,女孩就会带着来自她恋人的孩子去她丈夫处,这个孩子将被视为这个合法婚姻的第一个孩子。就男方而言,一个男人可以娶数名妻子,如果她们离开他,他仍是她们生育的所有孩子的合法父亲。
某些非洲民族也有同样的情况,当男人的妻子或妻子们离开他,他有权成为这些妻子未来孩子的父亲。只要在她们成为母亲之后,和她们发生产后第一次性关系,这份关系就决定了谁将会成为下一个孩子的合法父亲。一个男人娶了一位不孕的女人,能够以无偿或以依约付款的方式,从一个有生殖力的女人处得到她指定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女人的丈夫是精子捐赠者,而女子出借她的肚皮给没有子嗣的另一个男人或夫妇。尽管出借子宫是否应该免费或者可以计酬在法国引起热烈的讨论,但在非洲,这个问题并不存在。
苏丹的努尔人(Nuer)则将不孕的女人视同男人,因此她可以与另一名女子结婚。尼日利亚的约鲁巴人(Yoruba)认为,有钱的女人可以为自己购买许多妻子,和一位男人共同生活。孩子出生时,这个女人,法律上的“丈夫”,可以要求拥有孩子,或者可以将孩子以有偿方式让渡给亲生父母。在第一种情况下,夫妇是由两位女人所组成,她们是文字意义上的同性恋者。她们借助人工生育的方式拥有小孩,其中一名女性将是法律上的父亲,另一名则是生物学上的母亲。
古代希伯来人间常见的迎娶寡嫂制度,在今日世界仍然普遍存在。这个制度允许(有时甚至是强迫)弟弟为死去的哥哥生育,等同一种死后(postmortem)授精。更明显的例子是苏丹努尔人所谓的“鬼”婚:如果一个男人去世时未婚或尚无子女,近亲可以用死者畜养的家畜换购一名妻子,然后与这个女人一道为死者生育一个儿子(近亲则将这个儿子视为侄子)。有时,换成这个儿子为他生物学上的父亲——但在法律上是他的叔叔——执行同样的任务。他所生育的孩子则是他法律上的堂弟。
在所有的这些例子中,儿童的社会地位是根据法定父亲而决定的,即使“他”是一名女性。孩子知道他亲生父母的身份,他们之间的情感联系将他们联结在一起。与我们所担心的相反,信息的透明并不会引发儿童因生物学上的父亲和社会关系上的父亲不同而产生冲突。
在西藏,存在着几个兄弟共有一名妻子的例子。所有的孩子都被分配给最年长的兄长,孩子们称他为父亲,称呼其他人为叔叔。他们并不知道实际的生物性亲缘关系,但也不认为那是重要的。相同的情形也出现在亚马孙的图皮-卡瓦希伯人(Tupi-Kawahib)身上,我研究这个民族已经有五十年:一个男人可以娶姐妹中的几位,或者娶一名母亲以及她在前一段关系中所生的女儿。女人们一起养育小孩,似乎一点也不在乎她们所照顾的孩子是她己身所出,或是丈夫的另一名妻子所生的孩子。
生物性亲缘关系和社会性亲缘关系之间的冲突,令我们的法律学者和伦理学家感到困惑,可这种困惑不存在于上述的社会中。它们认为社群是最重要的,在其群体意识形态或者成员信仰中,生物性亲缘与社会性亲缘并无矛盾。然而,我们也不会因此认为,我们的社会必须根据这些异国例证来形塑自己的行事方式。但通过这些例子我们至少可以得知,人工生殖的问题有很多不同的解决方案,没有任何一个应该被视为自然的或者不证自明的。
其实,并不需要那么遥远的例子才能说明事理。关于人工生殖,我们主要
转载请注明:http://www.oohkt.com/wacs/9552.html